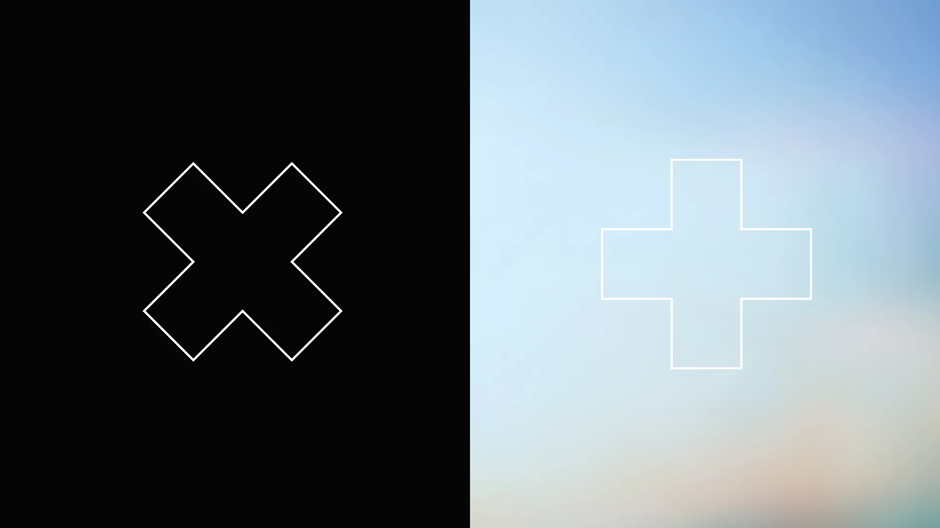
「你知道嗎,邁克,我曾是個同性戀,」我說。
當這些話從我嘴裡笨拙地落下時,邁克的刷子停下來了。那是1997年的夏天,我正開始攻讀歷史神學博士學位,而邁克在為我所居住的聖路易斯公寓進行粉刷。
他當時在和我聊學業情況,我們開始討論信仰問題。邁克剛向我解釋,他覺得自己永遠無法去教會,因為他是個同性戀。
「我知道他們說『改變性傾向』是不該發生的,」在我丟出這個震撼彈後,我繼續說。「但這就是我的故事。」邁克放下油漆桶,輕輕地把畫筆平放在桶的邊緣上,興致勃勃地盯著我看。
回想起和邁克的那次相遇,我可以看到,那段對話具有後來被稱為「脫離同性戀運動(ex-gay movement,以下簡稱「脫同」)」的所有特徵,而我曾經是這個運動的熱衷支持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使用了這個運動經典的台詞:「我曾經是個同性戀。」這句話暗示著我如今不再是同性戀了。我有個見證,一個關於放棄同性戀的故事。
需要說明的是,在那一刻,我和之前一樣完全只被男性吸引。我仍然處於金賽量表(Kinsey scale)的頂端。這是自1940年代以來用於分類性取向的研究工具。我說我「脫同」單純是因為我當時使用了那個運動裡最常說出的台詞。我曾試圖說服自己相信「我是個患有一種稱為同性戀的病的異性戀男性——這種病是可以被治癒的,」而且我已被治癒了。
我使用的「治癒」術語是「轉化療法(conversion therapy)」的ㄧ部分。出埃及國際(Exodus International)的第一任執行董事艾倫·梅丁格(Alan Medinger)形容這種治療為「自我認知的改變,即ㄧ個個體不再認為自己是同性戀。」他們認為人的性傾向完全只與他的「自我認同」有關。是我們對自己人生故事的敘述方式定義了我們自己。根據脫同運動的框架,我對邁克說的「我已『脫同』」並非說謊,因為我如今確實找到了一個新的自我認同:
我曾是一個「脫同」者。
1976年的出埃及組織的出現為福音派開啟了「治癒同性戀」的希望之路。創始人弗蘭克·沃頓(Frank Worthen)解釋說:「當我們創立『出埃及國際』時,預設的前提是上帝可以把人的同性戀性傾向變成異性戀。」隨之而來的是長達數十年對數十萬人的實驗。在出埃及國際負責人艾倫·錢伯斯(Alan Chambers)於2012年發表聲明,說超過99%的客戶的性傾向未曾真的被改變後,「脫同」運動就崩塌了。
雖然將治癒正規化的努力失敗了,卻仍在福音派中間陰魂不散,因為主流教派裡的一些人仍試圖將這類嘗試制度化。近期,保守的英國聖公會和長老會就某人是否可以稱自己有「同性戀身份」進行了辯論,這只是多年來在教會走廊裡回蕩的同類型辯論的最新一輪。畢竟,在轉化治療流程裡不可少的第一步,便是要人放棄「同性戀的自我認知」。
這種做法的一個成效是,規定非異性戀的信徒要躲在面具後面,假裝自己不是同性戀。這是修復過程的一部分。
但這種神學上的創新是近代的發明物。在「脫同運動」的治療模板出現以前,基督教古老的正統實踐裡已有一種關懷非異性戀基督徒的範本。
我曾好奇,當盧雲(Henri Nouwen)談及「關懷(care)」和「治療(cure)」之間的區別時,他想著的是否是自己的同性戀性取向。在邁克爾·福特(Michael Ford)為盧雲寫的傳記《受傷的先知》裡,邁克爾·福特(Michael Ford)記錄了盧雲如何在他的密友圈裡分享他身為獨身主義同性戀男子的經歷。盧雲曾嘗試透過心理學和宗教的方法來改變自己的性取向,但都無濟於事。他知道,出於對神的順服,他不能涉入性關係。但他的道路上充滿了孤單、無法實現的渴望,以及許多淚水。
在《心靈麵包》書中,盧雲寫道:「關懷一個人是陪伴他、和他同哭、同患難、同理他的感受。關懷就是同理他人。我們同理他們的時候,闡述著這個真理:這個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是個人,且是個凡人,是脆弱的,就像我一樣。」
他堅持道:「我們通常無法治癒他人,但我們總是能關心照顧他人。」
包括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在內的福音派領袖,為我們奠定了教牧關懷範本的基礎。斯托得——這位被BBC暱稱為「新教教皇」的神學家和作家認為,性取向是構成一個人的其中一部分。早在1982年,斯托得就在《今日基督徒面臨的問題》書中寫道:「在關於同性戀的任何討論中,我們必須嚴格區分『存在(being)』和『行為(doing)』的差別,也就是說,我們應區別一個人『自我認同』和『實際行為』之間的不同、『性取向』和『性實踐』之間的不同、『本質』和『行為』之間的不同。」
對斯托得來說,同性戀取向只是同性戀基督徒身份的一部分——一個墮落的部分(如同其他罪一樣),但福音並沒有抹去它,而是使用這部分讓這個人謙卑。
這種立場甚至可以追溯到比斯托得更早的時期。魯益師(C. S. Lewis)在1954年一封寫給范謝頓(Sheldon Vanauken)信中提到了一個「敬虔的男同性戀者」,且沒有認為這個形容詞有任何矛盾之處。魯益師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亞瑟·格里夫斯(Arthur Greeves)是個同性戀。魯益師稱他為「我第一個朋友」並向他明確表示他的性取向永遠不會影響他們的友情。魯益師寄給格里夫斯的信被彙編成《他們站在一起》一書,長達592頁。
在美國,當1969年紐約石牆暴動宣告著同性戀權利運動的誕生時,正統的基督教新教徒已開始探索《聖經》為同性戀者提供了什麼樣積極的願景。1970年InterVarsity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匿名的書籍《愛的歸返:一位基督教同性戀者的書信》,描繪了一條關愛之路,並受到斯托得的推廣。該書的獨身同性戀聖公會作者提及,他在寫這本書時仍是處子之身。
福音派的領導人知道教會內有一段需要充滿苛待、需要反思的歷史。在1968年寫給歐洲一位牧師的信中,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哀嘆教會是邊緣化同性戀的共犯。這位牧師見到至少六位同性戀自殺,他寫信尋求薛華的建議。「同性戀往往被排擠在人類生活以外(尤其是正統的教會生活),即使他們沒有實踐同性戀行為時也是,」薛華哀嘆道。「我認為教會這種行為既殘酷又錯誤。」確實,薛華的事工吸引了許多糾結於基督信仰的同性戀。
像薛華這樣的領袖更加厭惡的是那些濫用職權的宗教領袖。當老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 Sr.)私下向薛華提到同性戀的挑戰時,薛華說,這個問題很複雜。正如薛華的兒子弗蘭克在接受NPR採訪時以及在其《為神瘋狂》一書中所述,法威爾隨後回應:「如果我有一隻狗做了他們做的事,我會射殺它。」法威爾說這句話時並非在開玩笑。
事後,薛華對他的兒子說:「法威爾真的很噁心。」
「與性相關的罪(sin)不是唯一一種罪,」斯托得寫道,「甚至也不是最嚴重的罪;驕傲和假冒為善肯定更糟糕。」
1980年,斯托得組織了一次聚會,邀請英國聖公會福音派人士一起討論如何牧養同性戀。他們首先公開悔改自己曾對同性戀人士犯下的罪。這些領袖共同發表一份宣言:「我們因自己曾有極為傷人的『恐同症』而悔改⋯⋯這種偏見影響了我們之中太多人對同性戀人士的態度,我們也呼籲其他基督徒肢體有同樣的悔改。」
這是一份讓社會大眾十分震驚的宣言,因為那是個世俗社會輿論仍對同性戀抱有強烈偏見的年代。這份宣言並非發表於21世紀,不像在今天的文化裡,許多基督教領袖悔改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更符合現今的價值觀、有能力包容各種事物。當年,斯托得和這些福音派領袖,肯定是為著自己曾傷害了鄰舍及在基督裡的肢體而感到悲痛及悔改。這份宣言裡呼籲,在信仰生活上有資格成為神職人員候選人,且沒有實踐同性戀行為模式的基督徒應以正常規章流程被教會按立。
在這份宣言發表的五年之前,許多人對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師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類似的言論感到震驚,其中一些言論於1975年被報導在《亞特蘭大憲報》上。葛理翰曾被問及他是否會支持同性戀者被任命為牧師。他曾回答,應該在聖經教導的一些評估資格下,根據「每個人的資質」來考量。 具體而言,他提到的評估資格包括「遠離罪,接受基督,在悔改後將自己委身於基督和事工,並接受適當的培訓以擔當此職務」。
耶穌基督的福音為同性戀者提供十分積極的願景(vision)。魯益師向范謝頓解釋說,「在同性戀傾向一事上,就像在其他每一種磨難中一樣,上帝的作為可以得到彰顯。⋯⋯每個人身上任何一種殘缺都隱藏著一種呼召——只要我們能找到這個呼召,這個殘缺就『必會成為榮耀的得著。』」
魯益師問道:「同性戀者的積極生活應該是什麼樣子呢?」這是任何一個信靠耶穌的同性戀者都會問的問題。
而我們聽到的答案常常都是以簡單的「沒有」起頭。
沒有性生活。沒有約會。沒有戀愛關係。通常還包括「沒有擔任」教會領袖的角色。
在像我這樣的人聽起來,我們有個叫做「沒有」的終身職業。
那麼,什麼會是「有」的呼召呢?福音為同性戀者在基督裡帶來的積極願景是什麼?
當我觀察魯益師、薛華、葛理翰和斯托德的生命和事工時,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們帶來這樣一個關於耶穌的異象:耶穌救贖的大能。耶穌洗凈我們,使我們得以潔凈; 耶穌把我們帶進上帝的家庭裡;耶穌掩蓋我們的羞恥,饒恕我們的罪;耶穌以我們的名字呼喚我們。耶穌了解我們靈魂的每一處,卻仍然希望與我們建立關係;耶穌與我們一起受苦,更為我們受苦;耶穌挑戰我們為祂的國度而活;耶穌給了我們新生命和其中所有的喜樂;耶穌是那田地裡的寶藏,我們為祂變賣一切,因為祂是我們永遠無法被人奪走的寶藏。
這就是耶穌,祂帶來的天國價值觀將我們捲進祂在宇宙間的作為,祂的作為遠超過我們自身。在基督裡,我們發現自己身處於一個更大的敘事裡。
這並不是在說,耶穌是任何人能變成異性戀並擁有溫馨的家庭的手段。祂就是上帝本身,是我們被造的目的。當我們有了這位真實的上帝,我們的盼望的核心不在於我們今世是否是異性戀,而在於終將到來的那一天,站在我們的救主面前的時刻。
如果沒有這種與救主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對異性戀者還是對同性戀者而言,談論《聖經》裡的性道德都沒有任何意義。沒有異性戀者會接受這樣的倫理,也沒有同性戀者會接受這樣的倫理,除非他們愛上耶穌。一顆被祂的恩典撼動過的心,不僅會願意,而且渴望跟隨為我們而死的那位。
薛華、葛理翰和斯托德都曾表示,他們相信有些人天生就是同性戀。這幾個基督教領袖都認同基督教歷史上對於《聖經》裡性道德的的教導及解讀。這意味著他們的觀點為人們應委身致力以符合上帝對創造物的設計來生活及行事。除了不同性別的兩人在一夫一妻制婚姻裡的結合外,他們不支持其他在性上結合的可能性。但他們以謙卑的態度和同性戀來往。
他們的異象並非齊頭式的「轉化」讓所有人接受其天生不具有的性衝動裡。相反的,他們認識到,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最大的掙扎點可能不在於性方面的罪,而是給予愛和接受愛的能力。因此,他們強調人們對於來自教會裡的團契、社區的需求,人們對深入的、長期性的友情的需求,以及對基督裡肢體家人情感的需求——即使是獨身者,也能被人理解、關愛。
斯托得本人是獨身主義者,他解釋道:「同性戀情形的核心是對人與人之間互愛的深刻且自然的渴求、對自己身份的尋求和對「成為完整的人」的渴望。如果同性戀者不能在『教會大家庭』裡找到這些東西,我們就不應該繼續講『教會大家庭』這個詞。」
魯益師、薛華、葛理翰和斯托德也同樣視同性戀狀況為一種無法「自己選擇」的取向,很難期望今生一定會得到改變。他們最為關心的是同性戀者在情感上和關係上的需求。薛華在1968年的信中堅持認為,教會需要成為教會,並「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幫助這樣的人。」
在NPR的採訪中,薛華描述他父親在瑞士的事工L’Abri是一個「歡迎同性戀——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的地方。」他補充說:「在父親的事工禾場裡,沒有人會跟這些人說他們必須改變(性取向),或者說他們是糟糕的人。你知道嗎,他們真實經歷了我父親如同基督般美善的同理心。」
1978年,舊金山一間正統長老會被起訴了,原因是他們解僱了一名違反教會行為準則的同性戀僱員。從這個事件裡,薛華預見到將來會有的重大文化變革。在《福音派大災難》中,薛華說,如果其他教會認為自己可能不會面臨同樣的挑戰,那就太傻了。
不過,薛華和葛理翰並不推薦「我們」與「他們」之間對立的分法。就在1964年總統選舉前幾週,一起同性戀性醜聞震驚了全國。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的最高顧問沃爾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因在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廁所裡發生同性性行為而第二次被捕。葛理翰打電話給白宮,為詹金斯求情。
在電話錄音中,葛理翰要求約翰遜總統對詹金斯表示同情。
1997年,在舊金山的一次佈道會上被問及同性戀問題時,葛理翰對記者說:「人的罪還有其他許多種。 為什麼我們要對這種罪火力全開,好像它是最大的罪?」 他補充道:「我有這麼多同性戀朋友,而且我們一直都是朋友。」當晚,葛理翰在牛宮(Cow Palace)對一萬名觀眾講話時宣布:「無論你的背景是什麼,無論你的性取向是什麼,今晚我們都歡迎你」。
正如斯托得在《問題》一書裡熱切強調的那樣,跟隨耶穌的同性戀者必須倚靠信心、盼望和愛生活:信心在於,相信上帝的恩典和祂的準則;盼望在於,眼目能超越今世的掙扎,看到我們未來的榮耀;而我們賴以生存的愛,必須來自基督屬靈的家庭——教會。我們必須依靠來自教會的愛——即使教會在歷史上辜負了像我們這樣的人。
教會歷史學家理查德·洛夫萊斯(Richard Lovelace)1978年出版的《同性戀與教會》一書獲得了福音派領袖如肯·坎澤(Ken Kantzer,前CT編輯)、伊麗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查克·寇爾森(Chuck Colson)、哈羅德·奧肯加(Harold Ockenga)和卡爾·亨利(Carl F. H. Henry)的鼎力支持。這本書在今天的環境下可能顯得很激進,但在1970年代,它代表了一種跨越大西洋的新福音派主義異象。與右派的恐同症和左派的與世界妥協相比,洛夫萊斯提出來自基督的福音的挑戰:
有另一種和同性戀相處的方法,對教會和同性戀基督徒來說都更為健康,而且可以成為對世界非常重要的見證。這種做法需要雙重悔改:一方面是教會的悔改,另一方面是同性戀基督徒的悔改。首先,這樣的悔改要求同性戀基督徒有勇氣公開承認他們的性取向,並遵守《聖經》裡明確的準則,離棄同性戀性生活方式。.... 第二,這樣的悔改要求教會接受、尊重和培養這些沒有參與同性生活方式的同性戀基督徒,(如同對待異性戀基督徒那樣)秉公按立他們擔任事工領袖的職位。
教會支持公開承認但已悔改的同性戀基督徒擔任領袖職務,將會是對世界深刻的見證,表明福音的大能使教會擺脫對同性戀的恐懼,也使同性戀擺脫罪惡感及束縛。
只有福音才能為這樣的雙重悔改打開謙卑的大門。而這就是洛夫萊斯和亨利、奧肯加和艾略特、坎澤、寇爾森、魯益師、葛理翰、薛華、斯托得,以及一個年輕的同性戀福音派聖公會信徒的基督教異象——他不敢使用自己真實的名字,儘管他依然維持處子之身。
像這樣的基督徒屬靈長輩的想法是正確的。我寫這篇文章是為大西洋的這ㄧ邊(美國)教會尚未走上這條路而哀嘆。
1970年代末期,北美教會開始一個嚴厲難堪的轉變。北美的「脫同」相關事工帶著對「轉變性取向」的盼望以倍速增長。隨之而來的,是他們將盼望轉移至今生。 1980年代,隨著愛滋病危機對同性戀社區的打擊,福音派人士轉為擁抱「異性戀性取向給人的承諾。」世俗世界的「修復治療師」增加了一些臨床專業的可信度。「治療(cure)」的新道路取代了「關懷(care)」的舊道路。
然後,在和世界打文化戰爭的保守派發現,我們這些「脫同者」是他們很好的工具。我們證明了,如果同性戀者真的願意,我們可以「選擇成為異性戀」。畢竟,如果我們能變成異性戀,教會就沒什麼必要為自己的恐同症悔改了。教會只需要像我這樣的人維持住我們已經改變了的假象。
在那場徹底改變了西方性文化的文化戰爭後,對基督徒而言,這個世界還有更多需要我們為之悲傷的事情。交易式戀愛關係、隨時可拋棄的婚約,以及對「性別」和「性向」的定義皆已發生巨大的變化。
但保守的教會對自身悔改的猶疑不定並沒有改變。
當我看著福音派教會在探討性取向和自我認同等議題時,常常使用當年在反同志運動中已失敗過的同類型語言和論述時,我知道我們(教會)錯過了真正的戰場:我們周圍的文化已經使世人相信「基督徒恨同性戀」。
我們的使命是要證明他們是錯的。我們應證明基督徒不恨同性戀。
全世界都在看教會是怎麼做的。我們的子孫正在觀察我們。他們已經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信仰,因為他們聽到周圍的人說基督徒討厭同性戀,而他們不知道會眾中誰受同性吸引且忠於基督,以及他們是否因此身份被愛和被接納。也許他們可以從言行舉止間觀察出來。但即使這樣也很罕見,而且可能冒犯人。
我並非在說我們有可能失去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那是必然的。
我想說的是,我們正面臨著失去下一代的風險。
對於那些願意聆聽的人,上一輩的基督徒領袖仍然願意並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該如何做。
格雷格·約翰遜(Greg Johnson)是聖路易斯紀念長老會(Memorial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師,也是《仍需關心:我們可以從教會治癒同性戀的失敗嘗試中學到什麼》的作者。
翻譯:LC, 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

Annual & Monthly subscriptions available.
- Print & Digital Issues of CT magazine
- Complete access to every article on ChristianityToday.com
- Unlimited access to 65+ years of CT’s online archives
- Member-only special issues
- Learn more
Read These Next
- From the Magazine
 With his refusal to race on Sunday, the Scottish sprinter showcased a bigger story about Christians in sports.
With his refusal to race on Sunday, the Scottish sprinter showcased a bigger story about Christians in sports. - Editor's Pick
 French evangelical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show people Jesus at 2024 Olympic Games.Français
French evangelicals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show people Jesus at 2024 Olympic Games.França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