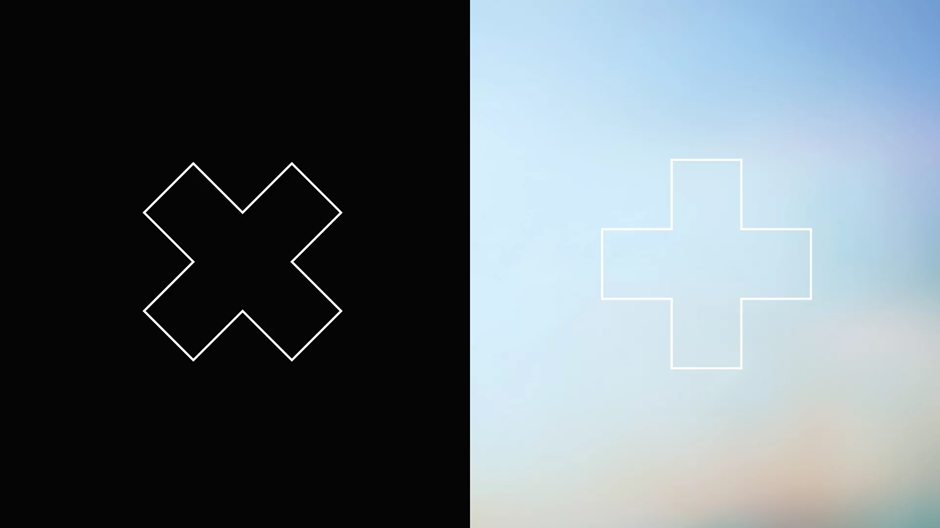
“你知道吗,迈克,我曾是个同性恋,”我说。
当这些话从我嘴里笨拙地落下时,迈克的刷子停下来了。那是1997年的夏天,我正开始攻读历史神学博士学位,而迈克在为我所居住的圣路易斯公寓进行粉刷。
他当时在和我聊学业情况,我们开始讨论信仰问题。迈克刚向我解释,他觉得自己永远无法去教会,因为他是个同性恋。
“我知道他们说『改变性倾向』是不该发生的,”在我丢出这个震撼弹后,我继续说。 “但这就是我的故事。”迈克放下油漆桶,轻轻地把画笔平放在桶的边缘上,兴致勃勃地盯着我看。
回想起和迈克的那次相遇,我可以看到,那段对话具有后来被称为“脱离同性恋运动(ex-gay movement,以下简称“脱同”)”的所有特征,而我曾经是这个运动的热衷支持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使用了这个运动经典的台词:“我曾经是个同性恋。”这句话暗示着我如今不再是同性恋了。我有个见证,一个关于放弃同性恋的故事。
需要说明的是,在那一刻,我和之前一样完全只被男性吸引。我仍然处于金赛量表(Kinsey scale)的顶端。这是自1940年代以来用于分类性取向的研究工具。我说我“脱同”单纯是因为我当时使用了那个运动里最常说出的台词。我曾试图说服自己相信“我是个患有一种称为同性恋的病的异性恋男性——这种病是可以被治愈的,”而且我已被治愈了。
我使用的“治愈”术语是“转化疗法(conversion therapy)”的ㄧ部分。出埃及国际(Exodus International)的第一任执行董事艾伦·梅丁格(Alan Medinger)形容这种治疗为“自我认知的改变,即ㄧ个个体不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他们认为人的性倾向完全只与他的“自我认同”有关。是我们对自己人生故事的叙述方式定义了我们自己。根据脱同运动的框架,我对迈克说的“我已『脱同』”并非说谎,因为我如今确实找到了一个新的自我认同:
我曾是一个“脱同”者。
1976年的出埃及组织的出现为福音派开启了“治愈同性恋”的希望之路。创始人弗兰克·沃顿(Frank Worthen)解释说:“当我们创立‘出埃及国际’时,预设的前提是上帝可以把人的同性恋性倾向变成异性恋。”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十年对数十万人的实验。在出埃及国际负责人艾伦·钱伯斯(Alan Chambers)于2012年发表声明,说超过99%的客户的性倾向未曾真的被改变后,“脱同”运动就崩塌了。
虽然将治愈正规化的努力失败了,却仍在福音派中间阴魂不散,因为主流教派里的一些人仍试图将这类尝试制度化。近期,保守的英国圣公会和长老会就某人是否可以称自己有“同性恋身份”进行了辩论,这只是多年来在教会走廊里回荡的同类型辩论的最新一轮。毕竟,在转化治疗流程里不可少的第一步,便是要人放弃“同性恋的自我认知”。
这种做法的一个成效是,规定非异性恋的信徒要躲在面具后面,假装自己不是同性恋。这是修复过程的一部分。
但这种神学上的创新是近代的发明物。在“脱同运动”的治疗模板出现以前,基督教古老的正统实践里已有一种关怀非异性恋基督徒的范本。
我曾好奇,当卢云(Henri Nouwen)谈及“关怀(care)”和“治疗(cure)”之间的区别时,他想着的是否是自己的同性恋性取向。在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rd)为卢云写的传记《受伤的先知》里,迈克尔·福特(Michael Ford)记录了卢云如何在他的密友圈里分享他身为独身主义同性恋男子的经历。卢云曾尝试透过心理学和宗教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性取向,但都无济于事。他知道,出于对神的顺服,他不能涉入性关系。但他的道路上充满了孤单、无法实现的渴望,以及许多泪水。
在《心灵面包》书中,卢云写道:“关怀一个人是陪伴他、和他同哭、同患难、同理他的感受。关怀就是同理他人。我们同理他们的时候,阐述着这个真理:这个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是个人,且是个凡人,是脆弱的,就像我一样。”
他坚持道:“我们通常无法治愈他人,但我们总是能关心照顾他人。”
包括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在内的福音派领袖,为我们奠定了教牧关怀范本的基础。斯托得——这位被BBC昵称为“新教教皇”的神学家和作家认为,性取向是构成一个人的其中一部分。早在1982年,斯托得就在《今日基督徒面临的问题》书中写道:“在关于同性恋的任何讨论中,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存在(being)’和‘行为(doing)’的差别,也就是说,我们应区别一个人‘自我认同’和‘实际行为’之间的不同、‘性取向’和‘性实践’之间的不同、‘本质’和‘行为’之间的不同。”
对斯托得来说,同性恋取向只是同性恋基督徒身份的一部分——一个堕落的部分(如同其他罪一样),但福音并没有抹去它,而是使用这部分让这个人谦卑。
这种立场甚至可以追溯到比斯托得更早的时期。鲁益师(C. S. Lewis)在1954年一封写给范谢顿(Sheldon Vanauken)信中提到了一个“敬虔的男同性恋者”,且没有认为这个形容词有任何矛盾之处。鲁益师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亚瑟·格里夫斯(Arthur Greeves)是个同性恋。鲁益师称他为“我第一个朋友”并向他明确表示他的性取向永远不会影响他们的友情。鲁益师寄给格里夫斯的信被汇编成《他们站在一起》一书,长达592页。
在美国,当1969年纽约石墙暴动宣告着同性恋权利运动的诞生时,正统的基督教新教徒已开始探索《圣经》为同性恋者提供了什么样积极的愿景。 1970年InterVarsity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匿名的书籍《爱的归返:一位基督教同性恋者的书信》,描绘了一条关爱之路,并受到斯托得的推广。该书的独身同性恋圣公会作者提及,他在写这本书时仍是处子之身。
福音派的领导人知道教会内有一段需要充满苛待、需要反思的历史。在1968年写给欧洲一位牧师的信中,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哀叹教会是边缘化同性恋的共犯。这位牧师见到至少六位同性恋自杀,他写信寻求薛华的建议。 “同性恋往往被排挤在人类生活以外(尤其是正统的教会生活),即使他们没有实践同性恋行为时也是,”薛华哀叹道。 “我认为教会这种行为既残酷又错误。”确实,薛华的事工吸引了许多纠结于基督信仰的同性恋。
像薛华这样的领袖更加厌恶的是那些滥用职权的宗教领袖。当老杰瑞·法威尔(Jerry Falwell Sr.)私下向薛华提到同性恋的挑战时,薛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正如薛华的儿子弗兰克在接受NPR采访时以及在其《为神疯狂》一书中所述,法威尔随后回应:“如果我有一只狗做了他们做的事,我会射杀它。”法威尔说这句话时并非在开玩笑。
事后,薛华对他的儿子说:“法威尔真的很恶心。”
“与性相关的罪(sin)不是唯一一种罪,”斯托得写道,“甚至也不是最严重的罪;骄傲和假冒为善肯定更糟糕。”
1980年,斯托得组织了一次聚会,邀请英国圣公会福音派人士一起讨论如何牧养同性恋。他们首先公开悔改自己曾对同性恋人士犯下的罪。这些领袖共同发表一份宣言:“我们因自己曾有极为伤人的‘恐同症’而悔改⋯⋯这种偏见影响了我们之中太多人对同性恋人士的态度,我们也呼吁其他基督徒肢体有同样的悔改。”
这是一份让社会大众十分震惊的宣言,因为那是个世俗社会舆论仍对同性恋抱有强烈偏见的年代。这份宣言并非发表于21世纪,不像在今天的文化里,许多基督教领袖悔改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符合现今的价值观、有能力包容各种事物。当年,斯托得和这些福音派领袖,肯定是为着自己曾伤害了邻舍及在基督里的肢体而感到悲痛及悔改。这份宣言里呼吁,在信仰生活上有资格成为神职人员候选人,且没有实践同性恋行为模式的基督徒应以正常规章流程被教会按立。
在这份宣言发表的五年之前,许多人对葛理翰(Billy Graham)牧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类似的言论感到震惊,其中一些言论于1975年被报导在《亚特兰大宪报》上。葛理翰曾被问及他是否会支持同性恋者被任命为牧师。他曾回答,应该在圣经教导的一些评估资格下,根据“每个人的资质”来考量。具体而言,他提到的评估资格包括“远离罪,接受基督,在悔改后将自己委身于基督和事工,并接受适当的培训以担当此职务”。
耶稣基督的福音为同性恋者提供十分积极的愿景(vision)。鲁益师向范谢顿解释说,“在同性恋倾向一事上,就像在其他每一种磨难中一样,上帝的作为可以得到彰显。⋯⋯每个人身上任何一种残缺都隐藏着一种呼召——只要我们能找到这个呼召,这个残缺就‘必会成为荣耀的得着。’”
鲁益师问道:“同性恋者的积极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任何一个信靠耶稣的同性恋者都会问的问题。
而我们听到的答案常常都是以简单的“没有”起头。
没有性生活。没有约会。没有恋爱关系。通常还包括“没有担任”教会领袖的角色。
在像我这样的人听起来,我们有个叫做“没有”的终身职业。
那么,什么会是“有”的呼召呢?福音为同性恋者在基督里带来的积极愿景是什么?
当我观察鲁益师、薛华、葛理翰和斯托德的生命和事工时,引起我注意的是他们带来这样一个关于耶稣的异象:耶稣救赎的大能。耶稣洗净我们,使我们得以洁净; 耶稣把我们带进上帝的家庭里;耶稣掩盖我们的羞耻,饶恕我们的罪;耶稣以我们的名字呼唤我们。耶稣了解我们灵魂的每一处,却仍然希望与我们建立关系;耶稣与我们一起受苦,更为我们受苦;耶稣挑战我们为祂的国度而活;耶稣给了我们新生命和其中所有的喜乐;耶稣是那田地里的宝藏,我们为祂变卖一切,因为祂是我们永远无法被人夺走的宝藏。
这就是耶稣,祂带来的天国价值观将我们卷进祂在宇宙间的作为,祂的作为远超过我们自身。在基督里,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更大的叙事里。
这并不是在说,耶稣是任何人能变成异性恋并拥有温馨的家庭的手段。祂就是上帝本身,是我们被造的目的。当我们有了这位真实的上帝,我们的盼望的核心不在于我们今世是否是异性恋,而在于终将到来的那一天,站在我们的救主面前的时刻。
如果没有这种与救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对异性恋者还是对同性恋者而言,谈论《圣经》里的性道德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异性恋者会接受这样的伦理,也没有同性恋者会接受这样的伦理,除非他们爱上耶稣。一颗被祂的恩典撼动过的心,不仅会愿意,而且渴望跟随为我们而死的那位。
薛华、葛理翰和斯托德都曾表示,他们相信有些人天生就是同性恋。这几个基督教领袖都认同基督教历史上对于《圣经》里性道德的的教导及解读。这意味着他们的观点为人们应委身致力以符合上帝对创造物的设计来生活及行事。除了不同性别的两人在一夫一妻制婚姻里的结合外,他们不支持其他在性上结合的可能性。但他们以谦卑的态度和同性恋来往。
他们的异象并非齐头式的“转化”让所有人接受其天生不具有的性冲动里。相反的,他们认识到,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最大的挣扎点可能不在于性方面的罪,而是给予爱和接受爱的能力。因此,他们强调人们对于来自教会里的团契、社区的需求,人们对深入的、长期性的友情的需求,以及对基督里肢体家人情感的需求——即使是独身者,也能被人理解、关爱。
斯托得本人是独身主义者,他解释道:“同性恋情形的核心是对人与人之间互爱的深刻且自然的渴求、对自己身份的寻求和对“成为完整的人”的渴望。如果同性恋者不能在‘教会大家庭’里找到这些东西,我们就不应该继续讲‘教会大家庭’这个词。”
鲁益师、薛华、葛理翰和斯托德也同样视同性恋状况为一种无法“自己选择”的取向,很难期望今生一定会得到改变。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同性恋者在情感上和关系上的需求。薛华在1968年的信中坚持认为,教会需要成为教会,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这样的人。”
在NPR的采访中,薛华描述他父亲在瑞士的事工L’Abri是一个“欢迎同性恋——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的地方。”他补充说:“在父亲的事工禾场里,没有人会跟这些人说他们必须改变(性取向),或者说他们是糟糕的人。你知道吗,他们真实经历了我父亲如同基督般美善的同理心。”
1978年,旧金山一间正统长老会被起诉了,原因是他们解雇了一名违反教会行为准则的同性恋雇员。从这个事件里,薛华预见到将来会有的重大文化变革。在《福音派大灾难》中,薛华说,如果其他教会认为自己可能不会面临同样的挑战,那就太傻了。
不过,薛华和葛理翰并不推荐“我们”与“他们”之间对立的分法。就在1964年总统选举前几周,一起同性恋性丑闻震惊了全国。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的最高顾问沃尔特·詹金斯(Walter Jenkins)因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厕所里发生同性性行为而第二次被捕。葛理翰打电话给白宫,为詹金斯求情。
在电话录音中,葛理翰要求约翰逊总统对詹金斯表示同情。
1997年,在旧金山的一次布道会上被问及同性恋问题时,葛理翰对记者说:“人的罪还有其他许多种。 为什么我们要对这种罪火力全开,好像它是最大的罪?” 他补充道:“我有这么多同性恋朋友,而且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当晚,葛理翰在牛宫(Cow Palace)对一万名观众讲话时宣布:“无论你的背景是什么,无论你的性取向是什么,今晚我们都欢迎你”。
正如斯托得在《问题》一书里热切强调的那样,跟随耶稣的同性恋者必须倚靠信心、盼望和爱生活:信心在于,相信上帝的恩典和祂的准则;盼望在于,眼目能超越今世的挣扎,看到我们未来的荣耀;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爱,必须来自基督属灵的家庭——教会。我们必须依靠来自教会的爱——即使教会在历史上辜负了像我们这样的人。
教会历史学家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1978年出版的《同性恋与教会》一书获得了福音派领袖如肯·坎泽(Ken Kantzer,前CT编辑)、伊丽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哈罗德·奥肯加(Harold Ockenga)和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的鼎力支持。这本书在今天的环境下可能显得很激进,但在1970年代,它代表了一种跨越大西洋的新福音派主义异象。与右派的恐同症和左派的与世界妥协相比,洛夫莱斯提出来自基督的福音的挑战:
有另一种和同性恋相处的方法,对教会和同性恋基督徒来说都更为健康,而且可以成为对世界非常重要的见证。这种做法需要双重悔改:一方面是教会的悔改,另一方面是同性恋基督徒的悔改。首先,这样的悔改要求同性恋基督徒有勇气公开承认他们的性取向,并遵守《圣经》里明确的准则,离弃同性恋性生活方式。 .... 第二,这样的悔改要求教会接受、尊重和培养这些没有参与同性生活方式的同性恋基督徒,(如同对待异性恋基督徒那样)秉公按立他们担任事工领袖的职位。
教会支持公开承认但已悔改的同性恋基督徒担任领袖职务,将会是对世界深刻的见证,表明福音的大能使教会摆脱对同性恋的恐惧,也使同性恋摆脱罪恶感及束缚。
只有福音才能为这样的双重悔改打开谦卑的大门。而这就是洛夫莱斯和亨利、奥肯加和艾略特、坎泽、寇尔森、鲁益师、葛理翰、薛华、斯托得,以及一个年轻的同性恋福音派圣公会信徒的基督教异象——他不敢使用自己真实的名字,尽管他依然维持处子之身。
像这样的基督徒属灵长辈的想法是正确的。我写这篇文章是为大西洋的这ㄧ边(美国)教会尚未走上这条路而哀叹。
1970年代末期,北美教会开始一个严厉难堪的转变。北美的“脱同”相关事工带着对“转变性取向”的盼望以倍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将盼望转移至今生。 1980年代,随着爱滋病危机对同性恋社区的打击,福音派人士转为拥抱“异性恋性取向给人的承诺。”世俗世界的“修复治疗师”增加了一些临床专业的可信度。 “治疗(cure)”的新道路取代了“关怀(care)”的旧道路。
然后,在和世界打文化战争的保守派发现,我们这些“脱同者”是他们很好的工具。我们证明了,如果同性恋者真的愿意,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异性恋”。毕竟,如果我们能变成异性恋,教会就没什么必要为自己的恐同症悔改了。教会只需要像我这样的人维持住我们已经改变了的假象。
在那场彻底改变了西方性文化的文化战争后,对基督徒而言,这个世界还有更多需要我们为之悲伤的事情。交易式恋爱关系、随时可抛弃的婚约,以及对“性别”和“性向”的定义皆已发生巨大的变化。
但保守的教会对自身悔改的犹疑不定并没有改变。
当我看着福音派教会在探讨性取向和自我认同等议题时,常常使用当年在反同志运动中已失败过的同类型语言和论述时,我知道我们(教会)错过了真正的战场:我们周围的文化已经使世人相信“基督徒恨同性恋”。
我们的使命是要证明他们是错的。我们应证明基督徒不恨同性恋。
全世界都在看教会是怎么做的。我们的子孙正在观察我们。他们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因为他们听到周围的人说基督徒讨厌同性恋,而他们不知道会众中谁受同性吸引且忠于基督,以及他们是否因此身份被爱和被接纳。也许他们可以从言行举止间观察出来。但即使这样也很罕见,而且可能冒犯人。
我并非在说我们有可能失去受同性吸引的基督徒;那是必然的。
我想说的是,我们正面临着失去下一代的风险。
对于那些愿意聆听的人,上一辈的基督徒领袖仍然愿意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该如何做。
格雷格·约翰逊(Greg Johnson)是圣路易斯纪念长老会(Memorial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主任牧师,也是《仍需关心:我们可以从教会治愈同性恋的失败尝试中学到什么》的作者。
翻译:LC, 吴京宁 / 校编:Yiting Tsai

Annual & Monthly subscriptions available.
- Print & Digital Issues of CT magazine
- Complete access to every article on ChristianityToday.com
- Unlimited access to 65+ years of CT’s online archives
- Member-only special issues
- Learn more
Read These Next
- Trending
 While we pray for peace, we need moral clarity about this war.
While we pray for peace, we need moral clarity about this war. - From the Magazine
 Alcoholism among women is rising. Can the church help?
Alcoholism among women is rising. Can the church help? - Editor's Pick
 Political violence looms large in our national history, to our shame. It does not have to define our future.
Political violence looms large in our national history, to our shame. It does not have to define our fu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