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基督教(或至少是它的某種形式——景教)於公元635年進入中國以來,它一直被視為外來宗教,因此與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或華人(cultural Chinese)不相干。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 “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口號更進一步加強和延續了這樣的誤解:一個人選擇跟隨耶穌,就意味着他放棄了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去追求一個外國或西方的神和意識形態。換言之,一個中國人向耶穌效忠,是對他的祖先和民族的一種極大的冒犯。
歷史學家吳小新認為,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宣傳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說法,而民族主義是造成對基督教的敵視的主要因素之一。任何熟悉19世紀中期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的人都會意識到這一說法所背負的歷史包袱。
與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繫
自19世紀以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基督教一直與西方帝國主義相聯繫。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基督徒是和帝國主義者一起來到中國的。許多西方傳教士都是乘着歐洲鴉片商的船舶,把基督福音帶到中國來的。
例如,早期來華的新教宣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為了將福音傳給更多中國人,加入了怡和洋行的鴉片船隊,擔任翻譯。前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在比較佛教和基督教進入中國的路徑時,形象地描述了這種歷史包袱。他說,在中國人眼裡,“如來佛是騎着白象到中國,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
鑒於現代宣教運動在中國開始時的這種情況,中國人反感西方傳教士的情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宣教士進入中國的大門,也是被西方軍事和海軍力量強行打開以擴大貿易的那扇門。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基督福音在中國人眼中受到了損害。
雖然基督教與西方帝國主義並不能等同,但在中國人的認知和記憶中,它們是同義詞。因此,在現代宣教的時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伴隨着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
儘管一些宣教士跟中國人在個人關係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不少宣教士成為外國勢力的代表,傷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中國人看到他們的土地被外國人侵佔,他們遭受了一個又一個的屈辱。他們開始將基督教視為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代表。
西方宣教士的正面貢獻
雖然不可否認,在中國歷史上的某個階段,某些自稱是基督徒的西方人參與了對中國人的壓迫和剝削,但我們需要將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與基督教區分開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人造成了很多傷害,但許多西方基督教宣教士也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許多宣教士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來為中國人民服務,並建立了學校、醫院和孤兒院等機構。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蕩年代,許多西方宣教士(如魏特琳)和醫生在大多數西方人撤離時留下來,冒着生命危險照顧受傷和死亡的人。
而在戰爭之前,許多基督教宣教士在19世紀在亞洲各地辦學,在建立中小學學校和大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多像英華書院和衛理公會的教會大學這樣的學校都是由理雅各(James Legge)、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宣教士建立的。著名的新儒家學者杜維明 指出,基督教大學的畢業生為中國幾乎所有的行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通過強調文科教育,這些學校培養了幾代現代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
把基督教當成是西方或西方人的宗教也並不符合事實,因為基督教信仰是上帝對全人類的拯救計劃,不分文化傳統或種族。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準確地說,早期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在東方而不是在西方。耶穌和他的使徒都不是西方人。雖然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基督教後來確實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但它實際上起源於亞洲。
與中國文化世界觀的衝突
除了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外,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也存在衝突。基督福音和它所代表的信仰對中國文化的世界觀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有人認為基督教的傳播是一種文化入侵。
中國基督教學者謝扶雅花了大半輩子時間分析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誤解和衝突的原因是基督教還沒有理解中國文化,因此造成中國文化也沒有完全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故此基督教未能給中國文化留下深刻印象和帶來深遠影響。
也許這過於簡化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但我認為在這樣做的時候,謝先生偶然發現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獨特之處。與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另一種外來宗教(佛教)不同,基督教是一種正統的、排他的宗教。它對上帝和現實提出了排他性的真理主張。佛教則在教義上顯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佛教能夠與中國的精神文化同化——適應並符合在中國本土的哲學。這導致佛教在中國產生了各種適應本土的變體,賦予它接近本土宗教的地位。
中國文化強調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這一點也進一步模糊了真理的客觀性。由於講述真相可能會涉及到讓對方不快的問題,中國人很難認真地探求真理。對中國人來說,講話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並保持愉快,比討論真相併冒犯他人更有美德。因此,中國人普遍不願意直接和公開地討論關於真理的問題。
像保羅那樣向中國人傳福音
那麼,為了有效地宣教,我們應該對認同中國文化的中國人採用怎樣的護教策略呢?我們也許並不需要一種特別的護教策略。畢竟,大使命並不是要針對所有非基督教的世界觀找出一種護教方法,而是要向世人見證耶穌基督,並奉他的名使萬民成為門徒。護教學只是一種方法論——我們需要清除可能阻礙人理解和接受福音的知識或文化障礙。
使徒行傳記錄了保羅在雅典的著名佈道。然而,在亞略巴古的講道之前,使徒行傳記載雅典人認為保羅是在向他們傳揚一位外國的神(徒17:16-20)。雅典人稱保羅是個胡言亂語的人,提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雖然這讓他們想了解更多。當然,我們的聽眾可能不會像雅典人那樣對我們的信息感興趣——畢竟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他們不願意花時間在信仰上較真。但是像保羅一樣,我們需要探尋出有效的方法,將他們的一些價值觀定位於基督教的世界觀中。
如果我們要與世界上人口超過13億的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分享基督教信仰,我們就需要了解他們的世界觀。我們有責任去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的世界觀和文化表達方式。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委婉地提出探尋性的問題,並在尋求聖靈的幫助以辨別核心問題時,學會專心聆聽。我們必須學習如何用對世界上這四分之一人口有吸引力和意義的語言來闡述福音。
I‘ching Thomas是基督教護教學作家和講員,專業研究基督教信仰與東方文化的關係。
本文是I‘ching Thomas著《耶穌:人類繁榮之路》(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一書第一章的節選,©2018。經Graceworks Private Limited出版社( www.graceworks.com.sg)許可使用。
翻譯:Sean Cheng

2018-02-01
142 pp., 1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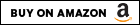

Annual & Monthly subscriptions available.
- Print & Digital Issues of CT magazine
- Complete access to every article on ChristianityToday.com
- Unlimited access to 65+ years of CT’s online archives
- Member-only special issues
- Learn more
Read These Next
- From the Magazine
 How I discovered God’s peace and found relief from debilitating anxiety.Português
How I discovered God’s peace and found relief from debilitating anxiety.Português - Editor's Pick
 How Jesus and the Powers, cowritten with Michael F. Bird, calls Christians into the political sphere.
How Jesus and the Powers, cowritten with Michael F. Bird, calls Christians into the political sphere.













